《欢喜》:在真正被公正对待之前,我们唯有不断言说
作者/
为什么当女性支持一些观念的时候,就变成了狂热分子呢?
你会说马克思是个狂热者吗?女人做的也是同样的事啊。
《欢喜:女性、革命和一个逝去的男孩》是意大利作家达契娅·玛拉依妮最近出版的一部作品,意大利原名为corpo felice,意为happy body,欢喜的身体。这是一本“介于想象与非虚构之间的个人书写”,是一场作者和她曾经失去的孩子之间的对话,也是一次对于哲学、艺术、神话、历史和日常生活中女性与女性身体的思考。

在阅读了玛拉依妮这部诚挚动人的作品之后,下文将尝试从生育、强奸和欲望三个主题切入,粗浅地谈论一些书中的话题。过去的几年,女性议题成为了最广为讨论的话题,甚至或许是一种被过度讨论的话题。那么,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今天继续谈论呢?我想,这只为了获得每一个人都应有的尊重,只是为了反抗不对等的权力关系,为了实现一个人人都生而欢喜的世界。在我们真正被看见、被听见、被公平对待之前,唯有不断言说。
一、生育:被剥夺的女性
生育,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“剥夺”母体的过程,所有输入的养分、经受的辛劳,都是为了孕育那个新的生命。然而,这种“剥夺”不只是停留在生理意义上,还在于更深远、更隐晦的层面中。
我们都知道,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,可是这种转变是如何实现的,女性又是如何一步步被塑造成今天的样子的?在母系社会,由于女人掌握着生育,所以她们获得了统治的权力。而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,正是因为男人开始掌握了生育,生育孩子逐渐转变成了男性一方的功劳,男性成了人类繁衍的主宰,女性的子宫不过是一具容器,上帝的种子才是生命的神圣起源。
希腊神话里,太阳神、火神、酒神等其他诸神是宙斯和不同女神(宙斯的表姐妹、姑妈)生下的孩子,他们因父之名彼此连结,具有各自不同的神力。
而智慧女神雅典娜更是直接从宙斯的头脑中诞生;

从宙斯头脑中诞生的雅典娜
图片源于网络,侵删
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中,俄瑞斯忒斯杀死了与他人通奸的母亲,却最终被判无罪,因为在众神看来他只是伤害了一具身体,这个身体卑微地容纳和保存父亲的种子,父亲才是生命真正的繁育者;
天主教法令上,堕胎不被允许,人类的生命只有神圣的上帝才能掌握,而上帝是男的,圣母玛丽亚只是在上帝的允许下才以处子之身受圣灵感应而怀孕,她只是用来存放神灵的容器;
不论是在神话、戏剧,还是法律中,这种通过对女性身体、女性性行为的控制,贬损女性生育权力的叙事话语,随处可见。
这是我们无法改写的历史和无法否认的事实,但作者依然试图告诉她的幽灵男孩“阿失”这样一个道理:一个能生育的身体,既能生出孩子,也能诞生出思想、 愿望、计划和梦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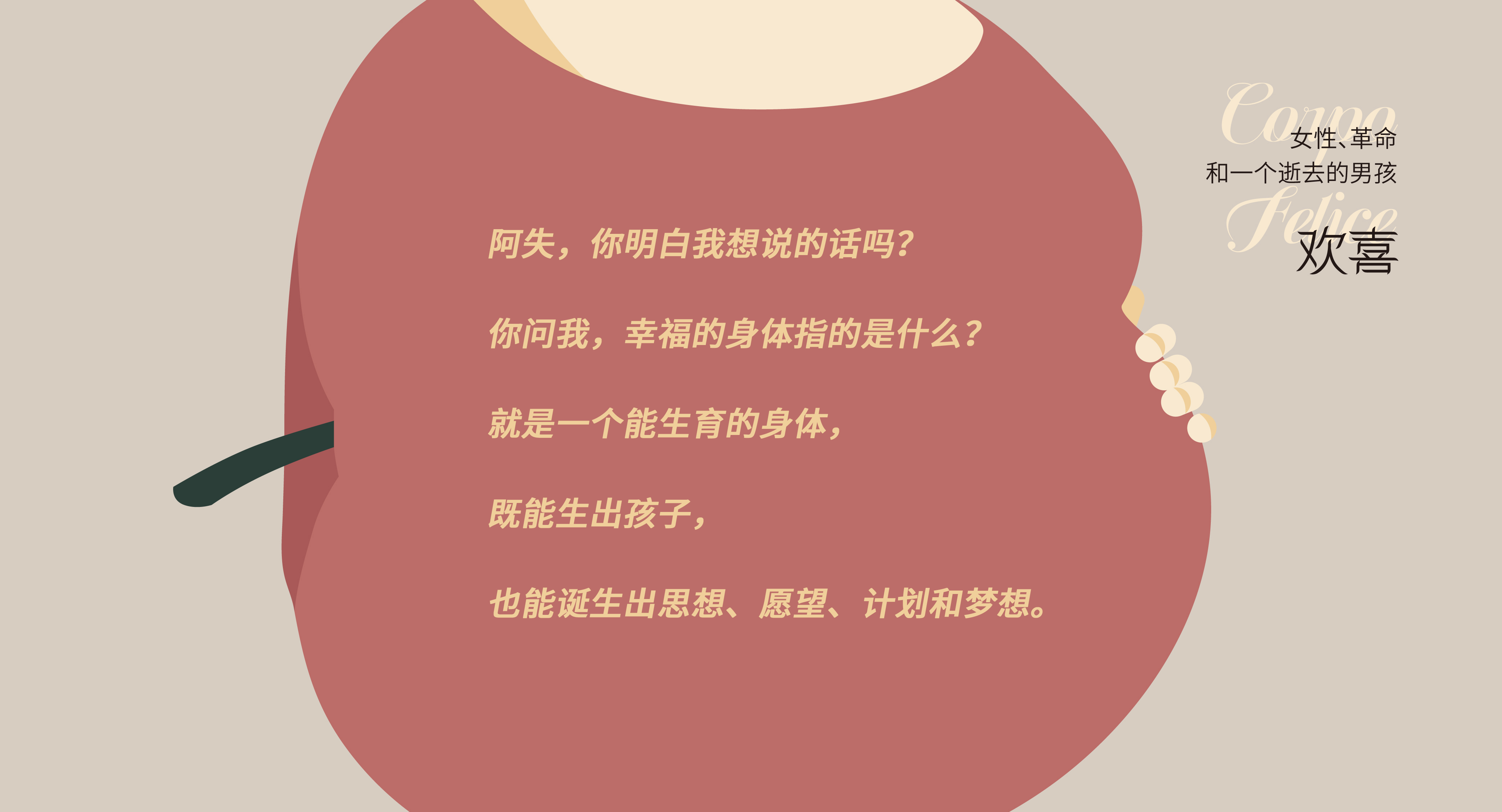
《欢喜:女性、革命和一个逝去的男孩》的正封是一位正在孕育生命的女性形象,
但它展开时,则是一个已经咬下的苹果——
象征着独立思想、意识的智慧果
二、强奸:“非人”的女性
在父权制社会中,社会的性别构成并非是“男性”与“女性”,而是“男性”与“非男性”,男性率先占据了标准人类的位置,其他的女性、男同性恋者、儿童只是位于“非人”的他者。正如上野千鹤子在《厌女》中揭示的那样:男性通过占有女性,使其成为性的客体,来取得其他男人的认同,以加入男性集团,从而成为“男性”。换句话说,在父权制社会里,所有未能成为男性的存在都是“非人”,只有man才能指代人类。
因为是“非人”,所以是不值得信赖的。在《欢喜》的开头,作者分享了一个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故事。在“我”六岁的时候,父亲冤枉“我”弄脏了一本“我”连碰都没碰过的书,即便“我”竭力辩解,甚至想要以死证明清白,父母还是更愿意相信“我”沾了墨水的手指,而非“我”说的话。
因为是“非人”,所以是可以随意对待的。女画家阿尔泰米西娅·真蒂莱斯基为了得到她想要的公正,必须要在被强奸后忍受在法庭上接受身体检查的二次伤害;卡蜜尔·克劳戴尔作为一名出色的雕塑家,她的作品不受认可,她的身心陷入与罗丹的爱恋纠葛中,饱受折磨,流产、背叛、被指抄袭,最终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,了此残生……这些不被公平对待的女性,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了很多,而在生活中,类似的故事依旧在继续发生。
 |  |
图左:阿尔泰米西娅·真蒂莱斯基最为著名的画作之一《朱迪斯斩杀赫罗弗尼斯》
图右:卡蜜尔·克劳戴尔在创作
图片源于网络,侵删
因为是“非人”,所以强奸也是无关紧要的。直到今天,在很多人的意识里,强奸犯之所以应该受到惩罚,不是因为侵犯了一个同样拥有主体性的个体、一个同样完整的人格,而只是因为违反了社会公德。如果你把那些比自己更脆弱、更贫穷、更边缘的存在,也看做是同样平等的生命,你还会肆无忌惮地实施那些暴力与伤害吗?

三、欲望:不可见的女性
最近,大家开始谈论起了新闻标题中的被动句式,认为这样的表达将(女性)受害者显露出来而隐藏了真正的罪犯。这样的讨论很好,也很有意义,但在很多其他的语境中,女性、女性的身体、女性的欲望,并非是那个显性的存在。
在一次访谈中,面对采访者“究竟什么是‘欢喜身体’”的问题,作者回答说在她看来目前并不存在所谓属于女性的“欢喜身体”,因为女性欲望虽然客观存在,但却没有一个可以使它变得合法、可以供大众分享的表达方式。长久以来,女性性欲只存在于自然界中,并不以形象、叙事、密码的形式存在人类社会。从绘画、小说到广告、电影,女性的欲望仍未被真正地言说,女性一直是欲望的对象,从来不是欲望的主体。
这让我想起了戴锦华老师在一次演讲中关于耽美的谈论。在耽美作品中,劳拉·穆尔维所提出的“凝视的快感”似乎被推翻,经典好莱坞电影中观众通过认同男性主人公的视点,从而将欲望的目光投射到女性角色身上的机制似乎不复存在。庞大的女性观众凭借她们巨大的消费潜力将以往镜头中被“凝视”的对象置换成男性,欣赏他们的颜值,占据他们的肉体,获得欲望的满足。
一方面,戴老师肯定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创作和女性力量;但另一方面,戴老师也和玛拉依妮一样,谨慎地指出:这些面向女性、由女性书写、承载女性欲望的耽美作品,却是以女性身体的缺席为重要的结构性条件。

学者戴锦华在造就TALK上的演讲
图片源于网络
这意味着,女性是在以男同性恋为载体,想象一种权力关系更加平等的情感关系;意味着女性依然没有可以表达自己、言说自身欲望的社会性模板;意味着女性在很大意义上依然是不可见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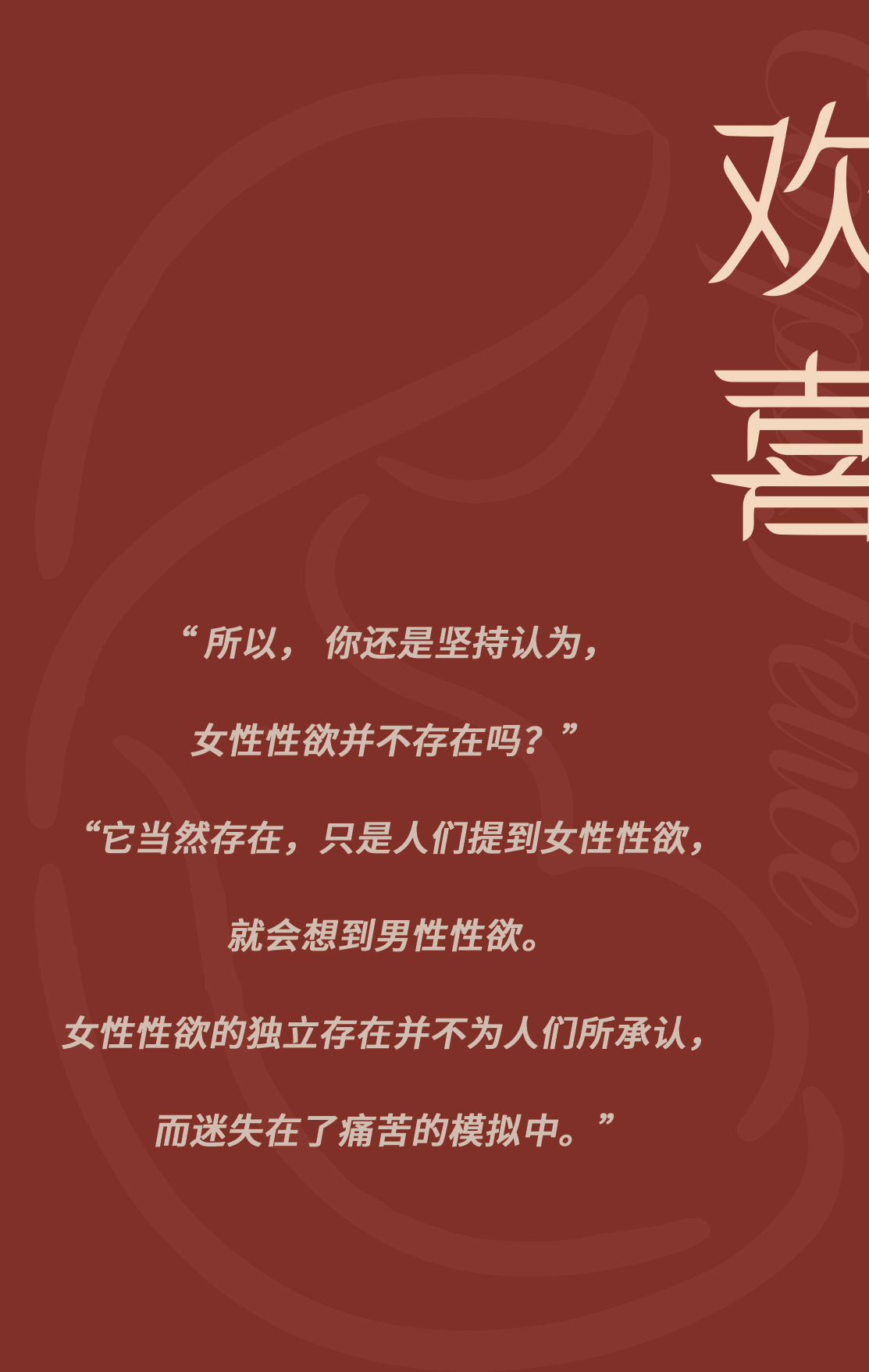
四、结语:女性还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吗
回顾过往的历史,女性走过了一条饱受剥夺的道路;注视当下的世界,女性依然在不被信任、不被看见、不被公平对待中挣扎,这不禁让人疑惑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?女性真的还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吗?
面对这样消沉致郁的疑问,作者在书中给出了她宽慰人心的回答。在她看来,“强者的胜利不意味着弱者的失败”,我们应该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得失。力量强大的一方固然暂时赢了,但并不意味着它的力量在走向理性和进步,也不意味着过往的努力和斗争没有意义。在真正被看见,真正被平等对待之前,我们唯有不断言说。
就像书中的叙述者,那个不断地在和她幻想中的孩子对话的女人一样,即便她所倾诉的对象心不在焉,即便周围的人认为她是在胡言乱语,她还是在不断地提问质疑,还是在不断地言说自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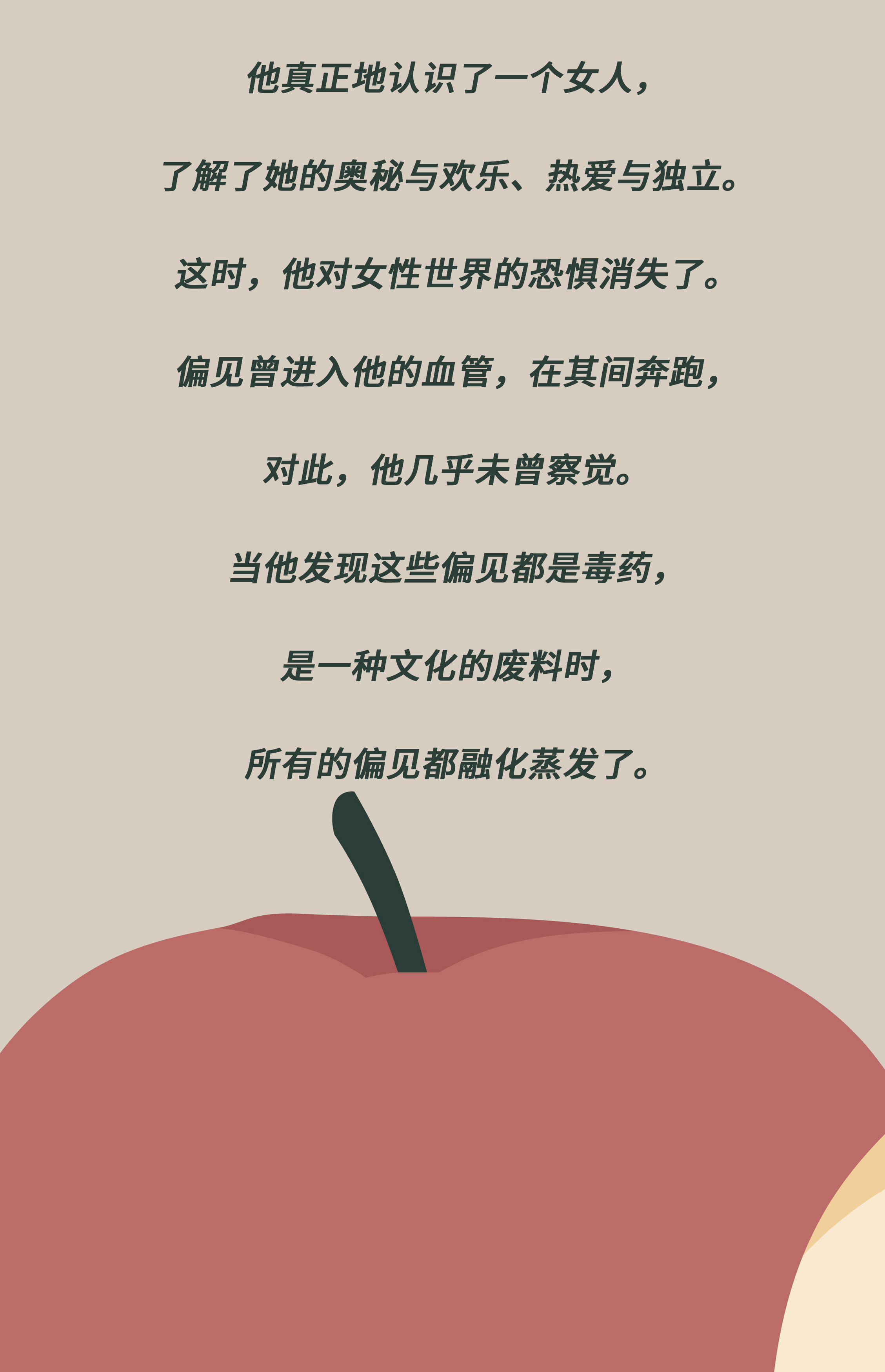
《欢喜:女性、革命和一个逝去的男孩》已开当当预售
点击下方链接购买
责任编辑:讷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