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履不停
作者/唐冲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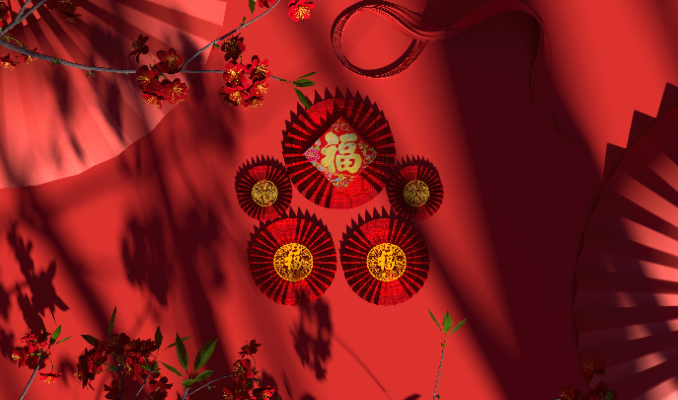
每个人都从各自的生活里抽离出来,造就一场热闹,让平凡的人当一次主角。
一
第一次参加春节的婚礼时,我还是个异乡人。
小时候,回老家过年是最难的事。我老家在川北大山深处,离大连两千五百多公里,没有直达的火车。通常的路线是先坐火车到沈阳,再转车去成都,再回老家县城,然后坐两个半小时乡镇巴士,三天两夜,格外漫长。打工的钱不好挣,差旅费,误工费,回乡的花销,来回奔波的疲倦,都是不回去的理由。好在老人也算开明,电话里说,节约点钱,过个节而已,我们又不是七老八十了,等你们能扎下根了,我们就到你们那里过年。于是我们一家人守在电话边,轮流跟他们说说话,讲自己的生活,讲明年的计划,算是拜了年。
在外扎下根,逃离贫瘠的故土,似乎是他们对父亲母亲最大的期望。
挂断电话后,父亲和母亲总是眼神空空地坐在床边沉默,像是虚脱。我少小离家,对我来说,故乡只是故乡,一个遥远的、并不具象的概念,一个可以用来造句的词语。我不知道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除了我们家,同在大连谋生的同乡还有三家人,一家做五金生意,大小算是老板,稍稍体面些,另两家跟我家一样,也是普通民工。我们几家人每年都聚。异乡人的春节,有几个能走动的故人是幸事。飘飘荡荡地活过一年,几家人围坐在出租屋里,尝尝老家的腊肠,聊着熟悉的方言,能让人踏实。
做五金生意那家,有个女儿,大我十三岁,没考上大学,辍学后一直在家里帮忙,我叫她蓉姐姐。大人们喝酒聊天时,她会带我出去玩。碰上有积雪,我们就堆出巨大的雪人,插上树枝和塑料红花,然后对着雪人许愿。她从不把愿望说出来,平时话也不多,像是藏着什么心事,我悄悄问过她是不是在谈恋爱,她只是笑着摇头。
有一年,堆好雪人,她问我想许什么愿,我说,想回老家,都快忘了我爷爷长什么样了,我还存了两百块压岁钱在他那儿呢。她愣愣,然后说,我也忘了。我很疑惑,因为她家每隔一年都会回去一趟,怎么会忘呢?她没再开口。许完愿,她带我买烟花,买完回去找大人要火机,他们正在屋里喝酒。她父亲醉醺醺地开玩笑,问我,你是哪儿的人?我想了想,说,大连人。他们都笑,只有蓉姐姐没笑。
我们去放烟花。烟花在雪地上绽开,她站在原地,盯着火焰,久久地出神,不知在想什么。
几年后的春节前,这个安静的女孩穿上婚纱,嫁给了一个大连本地人。
彼时她父亲的生意已经越做越大,婚礼的宾朋大都是当地人,老家人只有我们几家。我因为头一回参加婚礼,很兴奋,拖着收集的一大捆气球跑来跑去,直到响起音乐,注意力才被台上走出的人吸引。
新郎很普通,就像她一样普通,反而显得般配。她有些紧张,但仍落落大方,在接下来的流程里尽可能维持着从容。到敬茶时,一个衣着朴素、满头白发的老奶奶在司仪的搀扶下上了台,小心翼翼地在茶桌前坐下。茶桌另一边的椅子是空的。我正疑惑,她轻轻喊了一声,奶奶。声音里的从容消失了。老人答应,声音像枯萎的叶子,然后接过茶,从口袋里掏出红包递给她和新郎,不经意看向台下的人群时,眼神里分明是怯怯的躲闪。
我才忽然想起,她说过记不得她爷爷长什么样了。
司仪让老人讲两句,老人摆手拒绝,话筒还是递到了嘴边。大厅安静下来,老人嗫嚅许久,什么都没说出口。老人静静看着她,看了很久,然后默默下台,消失在人群里。她望向老人的背影,司仪提醒双方父母上台,她只好又回过头,继续流程。改口时,她已经明显有了哭腔,司仪对台下说,新娘子太激动了,再来一遍好不好?台下人跟着起哄。顿了顿,她对着新郎父母喊,爸,妈。台下鼓掌。她开始流泪。新郎抱住她。台下掌声更大。像一场热闹的表演。
我很不理解。她明明在哭。可她为什么哭呢?
很多年以后我才了解这段故事。婚礼上的老人,她的奶奶,不是亲生的。她父亲是捡来的孩子,长成少年时,老家兴起打工潮,于是独自走出大山,去寻起出路,寻起自己的命运。她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,父亲忙着工作,她就只好跟着爷爷奶奶长大。过了一些年,父亲做起了生意,娶了新的妻子,把她接到了大连,一直没再回去过,直到她爷爷去世后,才隔一年回去一趟。
那个老人独自在大山里,目送着少年成家立业,为人夫为人父,又目送着小女孩长大,离开,漂流到陌生的土地上,奔向她自己的人生。等老伴离开了,陪伴她的就只剩下大山、草木、河流与墓碑,她孤独地守望着这一切,守望自己隐没的人生。终于有一天,小女孩也要嫁人了,她七十多岁,还走得动路,也许下一次更大的事就是自己的葬礼。于是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她,独自买了票,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,来送小女孩最后一程。
得知这些时,也是春节前,那是许多年后,我在老奶奶的葬礼上最后一次见到了蓉姐姐。彼时她已经离了婚,带着女儿独自在广州生活,中间那些年,没回过老家,也没回过大连。她胖了很多,我没认出她,直到她离开我才知道那是她。她依然沉默。看样子,有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。
这么多年,我依然不知道她许了什么愿。
当年的婚礼结束后不久,我们几家人聚过一次,她丈夫没来。她父亲照例喝醉了,对我们讲述那些艰辛的过去,哭着说,终于扎下根了,终于走到今天了。他是个很坚硬的人,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这个男人掉眼泪。我想象着,那个独自离开家乡的少年郎,为什么会在漫长的岁月里被生活塑造成现在的样子,我以后又会成为怎样的中年呢。我想不出答案。
我和蓉姐姐像往年一样出门买烟花。途中我问她为什么会哭,她说,不知道。我说,你以后是不是不会回四川了?她摇头说,不知道。我说,结婚开心吗?她说,其实还是挺开心的。我说,你是不是有自己的家了?她看着我,问,你觉得我有家了吗?她眼神很真诚,这大概是个疑问句,没有其他含义。
我没回答。我不知道。
我说,我们要回四川了,我爸爸说以后不回来了。
她说,真好。
我点燃烟花,无端想起了那个老人。此刻她应该坐在大山角落的老屋里,一个人烤着炉火,望向空空荡荡的院子,她会想些什么呢。
她像从前那样望着燃烧的火焰,我想起了以前堆雪人的时候,今年没有雪,不知道她会怎么许愿。那时候她还是个女孩,今后她会去向何处呢。
烟花升空。她双手紧扣,仰起头,闭上双眼。
3,2,1,新年快乐。
二
母亲是个热爱生活的女人,认识父亲时就是。他们在大连相遇,自由恋爱,母亲会买同款的毛衣,织上同款的花朵,有了我以后,毛衣成了三件,花朵也织成三个,两个大的,一个小的。在外漂泊,每逢佳节倍失落,也总是母亲先打起精神,说,来,大扫除!父亲笑着应和。十平米不到的出租屋,一家三口挽起袖子,像要大干一场的样子。搬过几次家,到哪里她都能和邻居打成一片,我因此有了很多阿姨,红包糖果碟片漫画书,从没缺过。
他们离婚后,她留在东北,我跟着父亲回了四川。他们的感情破裂得很难看。那年他们三十岁出头,尚有稚气,一年不到就斗气似的找了下家。我还没从家庭破裂的现实里缓过劲,父亲的婚礼就开始了。
继母也是镇上的人,我叫她阿姨,她也有个孩子,大我几个月。临近春节,在外务工的人都回来了,婚礼没大操大办,但也热闹。我和同学在后院玩弹珠,继母的女儿或许不知道能去哪儿,怯怯地走过来,又不好意思开口,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。他们问,这是谁?我愣了半天,说,我姐姐。他们笑,天上掉个姐姐下来,以后娶了做媳妇。我发了火,用手里的弹珠砸去,他们作鸟兽散。
我和她坐在后院,大眼瞪小眼,不知说什么,最后还是她开了口,说,你妈妈呢?我说,在东北,你爸爸呢?她说,在广东。她张张嘴,似乎还想问什么,但没有开口。我们只好望着天空。
奶奶过来,叫我去帮忙,被爷爷拉住。爷爷吼她,什么场合你让他去?奶奶不甘示弱,就是要让他去。我不明所以,跟着奶奶去了。房前摆了二十几桌,坐满了人,有眼熟的,有不眼熟的。我第一次见父亲穿西装,原来他这么挺拔。他和阿姨正端着酒杯,挨桌敬酒。奶奶推我一把,说,你过去。于是我过去,走到父亲身边,下意识想抓着母亲的手,伸出手时才想起这是另一个女人了,只好缩回来。父亲看见我,给桌上的大人们介绍,我儿子。然后说,喊人啊。于是我跟着父亲说的称呼一一打招呼。大人们笑着,或许是似笑非笑,看着我说,真懂事。
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在这种场合被这种词语夸奖。我心里很难受,感觉自己要被他们的眼神淹没。
我撒腿就跑,听到父亲在身后喊了一声,也没停。跑到楼上,我用座机拨通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,过了几秒钟,电话通了。那头喂了一声。此前那种莫名的情绪才终于成了委屈,涌到眼睛里,我擦擦眼泪,把听筒使劲贴在耳朵上,生怕听不见声音,说,妈妈,爸爸结婚了,你快回来啊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,然后说,我不回来了,你要听话,快快长大。
她讲了很多,我心里难受,没听进去。挂了电话,我头昏脑涨,身体轻飘飘的,打开门,继母的女儿正站在门外。我朝她吼,你在这儿干啥,滚。她沉默,绕过我,走进房间,在书桌前坐下,说,我给我爸爸打个电话。我一下子清醒过来,有些愧疚,但不知该说什么。她定定地盯着座机,盯了很久,手却一直没按下去。半晌,我说,打啊。她还是愣着,回过头,带着哭腔说,我记不得他的电话号码了。
第二年春节,母亲结婚了。婚礼前她给我打电话,问我要不要回大连看看。我说,我住哪儿?她说,给你开个酒店。结婚前,她的婆婆指着她鼻子说,敢带着你那个儿子来,我就自杀。我知道,所以告诉她,我不来。她说,妈妈要结婚了。我说,我知道。她沉默一会儿,说,那你在家好好的。婚礼当天,我用她买给我的诺基亚给她发了条短信,妈,新婚快乐。她没回我。
几天后的除夕,星空璀璨,我爬到楼顶,给她打了通电话。我给继父拜了年,然后和她聊天,说老家的学校,说我的成绩。那天她也讲了很多,关于她,关于从前,没有母亲的姿态,更像在给一个久别重逢的老友诉说。
她小时候喜欢跟在舅舅屁股后面跑,人家问她长大了想嫁哪种人,她说不想嫁人,永远待在家里才好。人家就说,女孩子是别人家的。初中毕业,辍了学,揣着三百块钱和十几个煮鸡蛋坐上火车,看着窗外掠过的大世界,她心潮澎湃。初到大连,她在饭店做服务员,住在油污的阁楼上,一张行军床,一把椅子,一个编织袋。她在昏暗的白炽灯下哭着给家里写信,却从未寄出去过,因为始终记得那句话,女孩子是别人家的。
后来嫁给父亲,怀孕时听说父亲在外的不检点,又在日记里劝慰自己,日子总会好。有段时间,有个男人追求她,被她拒绝了,但他很执着。后来我得了一场大病,父亲在外面,家里没人管,她拿不出钱,那个男人掏了医药费。去成都看病时,男人一大早在车站接我们,白天跑前跑后,还给我买了身衣服,傍晚又送我们回火车站。母亲抱着我,说声再见,走进人潮里,他们从此再也没见过。回程的火车上,母亲抱着我站在窗前,默默地流泪。
漂泊的十几年,世事变迁,除了回忆,一无所有。
那个男人后来死在汶川地震里。跟继父结婚前,母亲做了一个梦,梦见他从父亲手里牵过她的手,又交到了继父手里,然后朝他们挥挥手,转身离开。
好像从来没真正拥有过什么,她说,明明那么认真地在活。语气很平淡。
在大连时,我们一家人很喜欢看星星。除夕时没有星星,我妈也会在墙上贴满亮片,像简易的星空顶。而那天夜里,我坐在屋顶的瓦片上,头顶的星空如此真实,我第一次感受到她,真正的她,我和她在同一片星空下。
她说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,我到下一程了。母子一世,走得再远也分不开。你要走好自己的路。
我说,有人在放烟花,你那边有吗?
她说,有,还有星星。
我说,妈,新年快乐。
她说,怎么不叫妈妈了?
冬夜的风吹来,我清醒了些,感觉自己有了力量。我没回答她。新年将至。我想我已经长大了,我再也不会害怕只能独自面对的漫长前路。
三
每年临近春节的日子,我都会想起一个特别喜欢的句子:人们忙着生,忙着死。萧红几个字就把人的命运写透了。这句话有种宏大而平静的悲凉,使人无力,却也因此有力。可惜我始终无法从中感受到具象的事物。我也不知道为何会想起它,或许是因为春节最大的特点就是匆匆忙忙。
前些日子,大伯家的哥哥结婚,我匆忙上路,赶回阔别许久的老家参加婚礼。我和本家的堂哥同行,他也很久没回去过。久别重逢,又近乡情怯,难免聊起从前。这些年家乡变化很大。乡镇学校的衰败越来越严重,小镇的中学只剩下几十个孩子,小学操场已经成了荒地,杂草丛生,教学楼里桌椅胡乱堆积着,只有几个退休的老教师还住在宿舍里。路好了很多,不用再担心泥泞,但车子却越来越少,因为几乎只剩下老人。往年还有孩子,但现在大家都卷,除非太穷,不然谁都不想自己孩子在那么荒凉的地方长大。
结婚的哥哥是建筑工人,九五年生人,十五岁离开学校,走上父辈的道路。他们远离家乡,在冰冷的人潮里沉默,建造起一座座辉煌的都市,给了无数人一个光鲜的家,唯独遗失了自己的故土。我和堂哥能对着电脑工作,已经算幸运,可何尝不是如此呢。我想世界或许变了,也或许没变。
聊到最后,话题从游戏、恋爱、玩乐变成了房子、车子、结婚。他说准备回南充买房,再看看工作,在成都一个月挣八千,活不下去,家里帮不上忙,他实在不想下半生像机器一样供一套老破小的贷款。我准备买车,跟他聊品牌和配置,又说起感情,他讲他相了几个亲,对方彩礼要价如何高昂,我讲前些日子遇到的女孩,让我动了结婚的心思。不知何时开始,这些事情忽然出现,像丝线,织成一张细密的网,围起我们的生活。他熟练地开车,像个大人,我想起小时候我们抢着骑一辆老二八大杠的样子,才清醒过来,原来已经2023年了。
没有外星人,没有大街上会飞的汽车,没有年少成名的风光,只是长大了,要面对未来,学着父母的样子一样和人交际。仅此而已。
高速上遇见一路婚车,又聊起此行主角。他是个很沉闷的人,逆来顺受。小时候成绩差,无心读书,让他辍学,于是十五岁就辍了学,让他去工厂,于是跟着大哥进了几年工厂。那几年浑浑噩噩,没攒下钱,没学到手艺,每年春节回家都被骂,也从来不反驳,只是沉默地听,然后说,晓得了。后来几年,他漂泊数地,东南西北都去过,还是找不到出路,最后只好随严厉的大伯去了广东,成了城市角落那些年轻的灰扑扑的民工兄弟。
家里倾尽全力,买了车房,剩下的只能靠他自己。他只好像从前那样默默接着,没说想要什么人生,也没说不想要什么人生。现在终于结了婚,对不对得起自己不知道,至少是完成了任务。
婚礼很简单,没请唢呐,没搭舞台,工程重心在婚房布置上。唐家虽然人丁兴旺,奈何全是男丁,手脚不细,一群男人对着绣花活抠脑袋,最后奶奶出面,叫来这些男人的媳妇,忙了一天,才把婚房收拾得像个样子。婚礼当天,他紧张得颤抖,不停喝水,接到新娘时,脊背笔挺,像个木偶。新娘子告别父母时掉了眼泪,他不知所措,只好给她递纸巾,回身到岳父母面前跪谢。终于回了家,他依然紧绷,接着是敬茶和拜堂,最后一步,夫妻对拜,他和新娘对视许久,终于活了过来,缓缓弯腰,从此成了一个丈夫。
众人欢笑,鼓掌,大喊,十分快活。
人们忙着生。
远处的奶奶戴着棉帽,望着仪式,轻轻笑着,背后是我家的堂屋,墙上挂着爷爷的遗照。那是另一段故事了。爷爷死后,她没找老伴,独自在老家生活,死活不去城里。这些年大伯家的两个堂哥成了家,大哥有了孩子,父亲事业顺利,我大学毕了业,家族往前迈步,而往事在时间里,被雨打风吹去。
那天山上办着婚礼,山下办着葬礼。葬礼的主角是爷爷的故人,我曾经骑摩托拉过他下山,他讲,你爷爷了不起哟,走得太早了。这些年里,一代人长大,一代人消亡。本来说家里有红事,不能去白事,奶奶坚持要去,说爷爷生前信基督,没这些讲究,老朋友走了不去送一送才是不讲究。于是我陪她下了山。山下的路上也停着许多车,各地牌照,看样子也是匆忙赶回来的。主人家披麻戴孝,地上零落着黄叶,一片萧索,山上山下像两个世界。
挂完礼,我扶着奶奶上山,走到山腰时,白事的唢呐班子猛地吹起哀乐,我随着奶奶回头望去,山间云雾缭绕,深冬的大地正在沉睡,只有人类还醒着。奶奶突然说,你爷爷死了九年了。这些年我们都在外地读书工作,奶奶独自在老家,没说过孤独,但有时会和爷爷的遗像说话。奶奶说,你也要快点成家,不晓得我还看得到不。山下的哀乐在山间回荡,经久不息。
人们忙着死。
婚礼结束,我坐车离开,那些赶回来的车子也一起离开。原本热闹的家门霎时冷清下来。回成都后,我接到奶奶电话,问我是否平安到家。我说,到了,你一个人在家?她说,嗯。我说,他们呢?她说,你爸爸去城里了,大伯和哥哥们都去亲家了。我想起她热闹过后孤零零坐在房前的身影,有些难受,但不知说什么,只好说,不早了,你早点休息嘛。她像是怕我挂了电话,急急地问,你今年过年回不回来?
我眼眶一热,几乎没忍住。
我说,回,肯定回,忙完就回。
她满意地说,好,那我睡了。然后挂了电话。
那一瞬间,我又想起了萧红那句话,接着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总是会在春节想起它。
记忆里的春节,就是吃不完的酒席。春节前后,结婚的人图热闹,濒死的人难熬过寒冬,红白事扎堆,人们团聚在一起,或庆祝,或送别。每个人都从各自的生活里抽离出来,造就一场热闹,让平凡的人当一次主角,无数种命运又在这种热闹里交织、膨胀,像一场盛大的舞台剧。繁华落幕后,人们相互告别,返回生活,再次启程,前往下一站。
春节本身也一样。生活漫长而颠簸,像潜在深海,时刻要提心吊胆,春节回了家,就是探出了头,看得见阳光和山脉,终于能大口呼吸,短暂清醒。但毕竟是短暂,眷恋再久,总要收拾好行李出发。
下一站有什么,谁都不知道。而终点是什么,每个人都清楚。
春运的人潮,高速的车流,国道的摩托,穿白纱的新娘,挂挽联的老屋,藏着多少人生呢。
人们忙着生,忙着死。如此具象。
四
但无法停止。
岁月无法抵挡,像逆着洋流游泳,触碰到鲜活事物的每一个瞬间,自然意味着上一个瞬间的消亡。故土的消亡,故人的消亡,情感的消亡,自我的消亡。好在还有此刻。可以选择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,往前往后还是往左往右,追逐欲望还是追逐月光,清醒着听听风声还是麻木着继续追赶。在未来面前,哪种选择都会有错,但也意味着,每种选择都是正确的,所以大可勇敢些,把故事继续讲下去。
团圆也好,新婚也好,送别也好,都是一次清醒的呼吸。生活也许是洪水,我们一次次倒下,但听听自己的呼吸声,总归还能站起来,再次向它敞开怀抱。我想这也是春节的意义。
新年快乐,朋友们。
愿我们路途漫长,步履不停,有枝可依。
责任编辑:梅不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