弹珠游戏
作者/予默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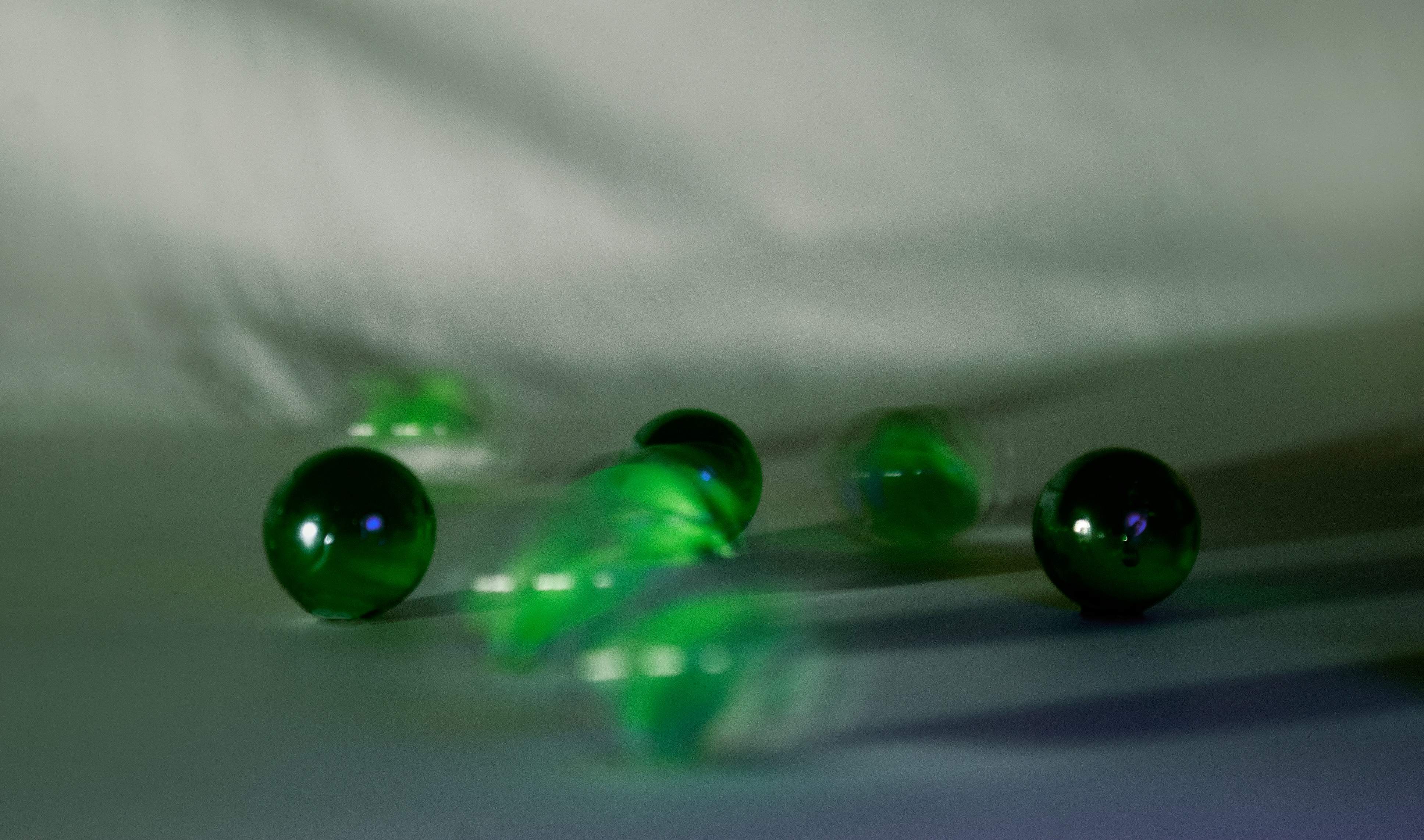
家遭变故,只有一个人可以继续念书,最终的抉择,由弹珠游戏胜负决定。
一
柳清和柳安从未见过母亲如此严肃的样子。她端坐在餐桌对面,摩挲着肿胀的指关节,来回端量姐弟二人。几个孩子叫嚷着穿过巷子,一只大黄狗在门口逗留,朝屋内探了探,吐着舌头离开了。“凭良心讲,”母亲终于开口,“我对你俩一向公平。”柳清皱起眉头,说:“妈,别绕弯子,赶快讲。”柳安环视客厅,想找出反驳母亲的证据。窗台上趴着两只铁皮青蛙,发条都坏了;鞋架上两双回力鞋是同一天买的,款式和颜色相同,唯独尺码不同。柳清有的,自己也有。母亲说得没错,她端平了这两碗水。
“不对。”柳安站起身,从柳清的椅背上摘下挎包,撂在桌上,说:“柳清的包上绣着朵花呢,我的没有。”柳清夺回包,说:“你的又没有磨破,到时候叫咱妈给你补一朵就是了。”柳安说:“我不要花,我要孙悟空。”
“说正事,”母亲用手肘捶了下桌面,“我没法去厂子干活了。”
二人同时发愣,掂量着这句话的分量。母亲说:“要不是老柳走得早,咱们现在也不至于考虑往后的问题。”
“什么问题?”柳清和柳安同时开口。母亲说:“柳安,那段时间你总是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,我正担心着,没想到你竟和柳清考了一样的分数。”她看向柳清,“如果老柳还在,他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你继续跳舞······”母亲停住话头,双手摊放在桌上,说:“哎,我该怎么向他交代啊。”
三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儿,母亲起身去厨房倒水。柳安趴在桌沿,支支吾吾地说:“她是不是要把咱俩送走一个?像二班刘辉的家里那样。”柳清说:“傻帽,咱俩有一个没书念了。”
上个月,两人都拿到录取通知书,是城里同一所重点高中。这张纸还没在枕头底下捂热,今天就得进垃圾桶了。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,前些天一连打了三个盘子,她说自己只是不小心。常言体内有疾,手指先知,柳清早已察觉到问题,却没想到母亲下岗得如此突然。
母亲找来姐弟历年的奖状,铺在桌子两旁,来回清点,生怕有疏漏。结果是柳清占上风,二十三张,比柳安多一张。柳安弓身拿起柳清的一张奖状,说:“进步之星?分明是凑数的,三张加起来都不如我一张优秀班干部奖。”母亲说:“哪能这样算?好歹都是荣誉。”
柳安跑上楼,取来一张纸。“既然如此,这张也算荣誉。”他在母亲面前摊开。这是以前父亲为柳安颁发的奖状,父亲剪下春联的一片边角料,用漂亮的楷体毛笔字写着:当代诗圣。“要是咱爸没走,我还能得好几张。”柳安撅起嘴望向窗外。“你还有脸讲这个?”柳清说,“要不是你,咱爸今天就能带我去文化宫看表演了。”
“不许提这件事。”母亲再次用手肘撞响桌子,“今天必须商量出结果,不然谁也别吃饭。”柳安说:“那我先提一嘴,听说舞蹈艺考的培训费很贵的,至少五位数,咱妈就算能分身也赚不来这笔钱。”柳清说:“我将来要跳上春晚的,等赚了大钱,加倍还给咱妈。你呢?写那些狗屁不通的烂诗,一斤顶多卖两毛。”
“你能跳上春晚,我就不能写进作协啦?”柳安抬高声音,“做梦也得讲求公平的,妈你说是不是?”母亲说:“你俩闹了这么多年闹够没有?这件事必须和和气气地解决。”她端起杯子嘬一口水,喉咙发出清晰的吞咽声,“算了算了,今天先这样。”
二
柳清回到卧室锁上门,对着床前的落地镜发呆。镜子是以前父亲买的,柳清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对镜练舞:立定,旋转,起跳,足尖点地,重现奶奶当年的舞姿,跳完《天鹅湖》跳《红色娘子军》。她眼神自信,姿态灵动,颇有奶奶在文工团时的风姿。每每这样舞起来便目空一切了,直到饥饿时才停下。父亲离世前一直尽力支持她的爱好,带她找老师,买各式舞裙。父亲从不奢求柳清跳出什么名堂,只为了看她在台上傻笑的样子。柳清却满怀理想,一心站上大舞台,给父亲争光。可是柳清觉得母亲刚才分明偏向柳安,自己的舞蹈梦岌岌可危了。她想起床底那双沾着血渍的足尖鞋。倘若不能继续念书,这些年的血都白流了。
这时门被敲响。母亲在外面小声说:“柳清,我进来一下。”柳清说:“我没心情,你找柳安去吧。”母亲叹了口气,走去了柳安的房间。不一会儿,柳清听见他们争执起来。她朝门外探出头看了看。柳安的房间在过道对面,门上贴了一幅海明威伏案写作的海报画,左下角是一张便签,用透明胶封住,写着:柳清禁止入内。母亲的声音从门后传来:“不管结果怎样,我都希望你俩好好相处,别总是闹别扭。”柳安说:“我和她冤家路窄,你就别费这心了。”
柳清和柳安的关系早在四年以前就破裂了。起初母亲并没在意,以为他们之间的冷漠只是父亲过世的余波。对于柳安耽误父亲上晚班一事,柳清一直怀恨在心。
四年前的冬至那天,柳清拿到了少年舞蹈竞赛的奖金。她邀上柳安,来到北街服装批发市场,买下了父亲相中已久的一件深棕色飞行夹克。以前父亲路过时总要拿起它放在身上比对一番,露出满意的神色,对自己说:“啊,这颜色好,料子也好。”可他从不舍得为自己花钱,永远都是比对一下就满足了。姐弟两人到店里时,那件夹克已经断码,只剩一件,卡其色。柳安觉得颜色太浅,工作时容易蹭脏,柳清说父亲才不舍得穿去干活。两人在店里争论很久,终于决定买下。
父亲傍晚从工地回家,看见挂历的钉子上挂着一件夹克,幸福地笑了,额头的泥灰都藏进了波浪般的皱纹里。穿上身发现码数偏小,袖口够不到手腕,衬衫的下摆长长地露在外面。父亲说:“不用退,过些年我的骨头一缩水,正好合身。”
柳安趁着父亲的高兴劲,说:“玩一局弹珠吧,你都多久没陪咱们了。”以前父亲清闲的时候,打弹珠是三人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,但自从他跟了刘工头之后,夜里加班成了家常便饭,弹珠局总是二缺一。若是少了父亲的参与,这场游戏就变了味,两人胡乱地弹球,为争输赢不择手段,最后总要闹得不愉快。
柳安揪住父亲的衣袖不放。柳清一脸不悦,说父亲累了一天,应该好好休息,不然没力气上晚班。父亲看了看钟,说不碍事,把两人推出了屋。
父亲的准头一向很好,与其说是比赛,倒不如说是父亲的个人才艺表演。他用结实的大拇指打出弹珠,一枚接一枚地命中目标,姐弟两人都输到只剩一枚时,父亲就会故意打歪,找借口说:“路灯太暗,没看准。”
这天父亲发挥照常,一连吃下了柳安的十九枚弹珠。他又找理由道:“起风了,下一个肯定得打歪。”柳安说:“回回都让着我们,多没意思?最后一颗了,痛快地赢我一局吧。”父亲说:“赢了又能怎样?你俩开心最重要。”只见他拇指一弹,弹珠慢悠悠地往前滚,停在了柳安那枚弹珠半寸远的地方。父亲站起时犯头晕,捶了捶脑袋,笑着说:“给你们留点翻盘的希望不好吗?”父亲把弹珠袋抛向柳安。两人看着他走进屋里换衣服。
那天夜里十点半,父亲被工友架着肩膀送回家中。他额头上一颗颗汗粒就像是撒了一地的玻璃弹珠。母亲问他是怎么了,他摇摇头,说只是有些累。父亲躺在沙发上睡了,再也没有醒来。
四年后的今天,柳清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父亲打出的每一道轨迹,每一次撞击都是那样清脆;父亲蹲下时,夹克被他的脊背绷得很紧;她还记得父亲临走前把夹克衫脱下,轻轻地掸灰,支好衣架挂回了挂历的钉子上。这一挂就是四年,背面的日历停留在1991年12月。
对母亲和柳安来说,这件夹克衫是个念想。柳清则不同,这是她钉在墙上的恨,对柳安的恨。要不是他那晚消耗了父亲的精力,家中的一切都会顺顺当当。母亲不至于积劳成疾,自己也不用面临辍学的窘境。
三
会议连续开了三天依然没有结果。母亲让两人列举各自的优势,制定今后的学习计划,设想未来的收入。讨论结果是柳安长大了要脚踩徐志摩,柳清要单挑杨丽萍。直到母亲的法槌敲响桌子,两人才从虚妄的幻想回到现实。
柳安知道自己毫无优势,在柳清面前只能靠语气稍稍占些上风。他早已厌倦这样的吹牛游戏。柳清多次参加校内外表演,屡获褒奖。而自己呢?自诩有文采,却从未被刊物录用稿件,甚至拿不出一篇高分作文。文学这种东西是超越时代的,今天写的垃圾,说不定会在将来被人奉为瑰宝呢。母亲和柳清哪懂得这个道理?唯独父亲愿意陪他写作,逐字逐句地推敲,给予中肯的评价。可是父亲已不在,抽屉中的几叠稿纸失去了最好的读者。这能怪谁?还不是自己犯下的罪过。
有一天吃完早饭,母亲还想继续开会,柳清当即找借口出门,柳安也找理由推辞,躲回卧室。柳安决心做最后的挣扎,他整理出近一年的诗稿,分成五份,每份五组短诗,塞进五枚信封。只要其中一首诗被出版社印成铅字,便能在母亲面前挺直腰杆。但想到等待的漫长,希望的渺茫,又将诗稿取出。也许柳清说得对,这些烂诗只适合挂上秤杆,按斤两衡量价值。
他记得第一次投稿是同父亲去的邮局。父亲为信封贴上邮票,两人各攥住信封的一角,对准邮筒。父亲说:“一,二,三。好了,未来的大作家很快要诞生咯。”四个月后,柳安收到了退回的稿件,父亲的预言没有成真。那天柳安久久地蹲在巷口的树下,生着闷气。父亲走来,说:“我刚刚又想了一遍,知道原因了。”柳安抬起头,看见父亲将两手背在身后,深情地朗诵道:
“秋日的寂静中,枫树轻轻摇曳。红色的舞裙,一片片坠落。枯枝划破北风,我听见天空的呜咽。”
父亲意犹未尽地品味了一会儿,捡起一片叶子,说:“我觉得这一节太伤感,看不见希望。”柳安说:“枯枝败叶的季节里哪有什么希望。”父亲说:“这就不对了,日子都是苦中带甜的,绝望和希望也能并存嘛。”
柳安把这首诗改写了无数遍,蚂蚁般的字爬一张张稿纸,始终解不开“希望”的奥秘。父亲离世以后,柳安更是觉得世上充满遗憾和感伤,所谓的“希望”都随着父亲埋进了土堆。
柳安终于将诗稿塞进信封。如果石沉大海,自己也认命了。他拿着信走到楼梯拐角,听见客厅里多了个人,是秦老师的声音。她在母亲面前称赞柳清的天赋,细数她获得的奖项。母亲陪着笑,不时说一句:“我知道,我知道。”秦老师撂下狠话:“柳清要是跳不进北京舞蹈学院的大门,我这辈子的老师算白当,你不能这么糊涂呀。”母亲说:“那我家柳安怎么办?让他辍学也是糊涂呀。”
柳安小心地退后两步。他没想到柳清居然这么快请来了救兵,有些懊丧。楼下传来玻璃的碎裂声。柳安手中的信没拿稳,掉落在台阶,滑到了客厅。这时柳清大声道:“将来谁更有出息,明摆着的。”楼下安静了好一阵。
“柳安,”秦老师说,“我知道你在上面,过来一下。”柳安下楼拾起信,塞进衣袋,绕开地面的碎渣,慢慢地挪到秦老师身边。秦老师捧起柳安的手,露出慈祥的表情。“你和柳清都是好孩子,将来一样有出息。”秦老师慢吞吞地说,“可你妈妈现在老啦,总得有人把这个家支起来不是吗?理想固然重要,但要先吃饱饭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。”柳安避开了她的眼睛,说:“为什么非得是我?”
柳清两手叉腰,不言不语。母亲把地面的碎渣铲进簸箕,也没再开口。午间的阳光把巷子的地面照得发亮,屋里却凉飕飕的。一阵风吹进窗子,墙壁上父亲的夹克摇摆起来,似乎想表达什么。母亲正要走上前将夹克重新挂稳当,那颗钉子突然挣脱墙壁,夹克连同挂历掉落在地。一枚淡绿色的玻璃珠从夹克的衣袋里滚出来,跑到了柳安脚边。
母亲“哎呀”一声,瞪大眼睛,露出惶恐的神情。柳清说:“咱爸显灵了。”
母亲对秦老师客气地笑了笑,请她改日再来。临走时秦老师对柳清叮嘱道:“千万要记得,你是舞的奴仆,这双脚走到哪就要跳到哪。”柳清点头说知道了。等秦老师走远,母亲关上大门,赶忙拾起弹珠,说:“你们觉得,这老家伙想表达什么?”柳清说:“他选了柳安呗。”母亲说:“我这就去请孙婆婆来看看。”
“没必要,”柳清说,“我去厂里踩缝纫机就是了。”
四
父亲显灵这件事在柳清看来纯粹是偶然,但她恰好借此了结母亲的优柔寡断。母亲的天平再这样摇摆下去,父亲真得从坟里蹦出来。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,没理由继续拖延。柳清本打算去制衣厂接替母亲的岗位,但想到自己还有一技之长,说不定能走出别的路子,就像秦老师说的,走到哪跳到哪。柳清找了家职业介绍所,求中介为她安排一份与跳舞沾边的工作。中介说:“在商场扮玩偶算不算?”柳清摇头,说自己愿意等。她每天一早守在介绍所的卷闸门前,失望之后就在附近闲逛,找一片树荫练舞。第五天,工作有了着落。“西二街那边有个戏班子招人,”中介说,“只要二十五岁以下的,说是跳什么……”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,“法国风情舞。”
柳清很快迎来了第一场商业演出,那是在肉菜市场前的空地上开展的洗发水促销活动。柳清接过主办方准备的演出服时,心凉了半截。一件露脐小背心,舞裙很短,只能勉强遮住臀部,而且红得艳俗。这要是被熟人看见,传到秦老师耳朵里可怎么办?往后都没脸见她了。
化妆师说:“又不是搞艺术,别挑剔了,老百姓爱看什么就穿什么。”柳清要求化妆师给她画得浓一些,要让人认不出自己。化妆师为她戴上一顶假发,说:“你都变身法国女郎了,谁还认得出来?”柳清觉得镜中的自己简直是个瓷娃娃,有些瘆人,头上的金色假发让她想起了母亲厂里的缝纫线。
柳清在演出开始前一分钟才走出化妆棚。舞台布置得很寒碜,远不如学校里的。背景墙是一位外国姑娘撩拨头发的广告图,旁边配文:法国洗发香波,专注受损发质修复。
与另外四位舞者登台后,柳清紧张地盯着地面,感觉这松松垮垮的舞台板随时会崩塌。身旁的姐姐说:“今晚最年轻漂亮的就是你了,自信点呀。”柳清冷笑一声。与其自信,她更应该自怜。主持人用中气十足的嗓门宣布表演开始,音响播放起《路灯下的小姑娘》,台下的两百来位观众纷纷吹响口哨。柳清不好意思将舞裙甩起来,主持人不停朝她使眼色,她这才加大了动作幅度。舞蹈表演结束后,主持人搬来五个箱子,让柳清她们到观众席售卖洗发水。观众一窝蜂地拥上来,似乎只对这五位金发女郎感兴趣。有人趁机捏一下她们的胳膊,碰一下手背。柳清慌了,忘记主办方要求她们不能说话的规定,她尖叫道:“把你们的臭手拿开。”观众立刻拉下脸来,说:“原来你们是假洋人,卖的肯定也是假洋货。”
促销活动在一阵嘘声中收场,主办方很是不满。多亏领舞的姐姐说了些好话,帮柳清保住了酬劳。散场后,柳清问领舞:“跳这种舞有什么意义?分明是为了满足男人的眼珠子。”领舞说:“我当年在省团跳舞的时候就想开了。你以为观众看的是水袖?是云步?他们鼓掌只是因为我长得漂亮。所以跳什么舞都一样。”柳清这时想起了秦老师的那番话,冷笑了一声。舞的奴仆?我今天是马戏团的奴仆,是一只猴子。
回到家里时柳清感觉有些尴尬。“法国舞女”的新身份在这清贫简朴的家中显得极不相称。柳安快步下到楼梯口,看见柳清后停住了脚步,惊慌地说:“还以为咱妈回来了。”他正要上楼,柳清从口袋里取出几张二十元递向柳安,冷冷地说:“等下,把这个交给咱妈,攒着当你的学费。”柳安站着不动。柳清说:“再跟她说一声,我去制衣厂干活了。”说罢将钱压在桌面的杯子下,回卧室了。
五
柳清身上的廉价香水味没能逃过柳安的鼻子。他知道柳清在撒谎,却怎么也猜不出那笔钱的真实来路。次日一早,他等柳清出门就偷偷尾随着。柳清走去西二街,拐进一条逼仄的小巷,敲开了发廊隔壁一扇玻璃门。柳安小心翼翼地躲在一辆三轮车后面,观察着屋内的动静。玻璃门贴着“漫舞文化”的字样,隐约听见里面播放着迪斯科舞曲,几位二十来岁的姑娘挤在一张大沙发上,抽烟闲聊。柳清坐在她们一旁,似乎有些拘谨。不时有人经过,隔着玻璃打量。待到下午,她们几人终于离开沙发,排成一列,在一位高个子女士的指导下练舞。柳清的身体显得僵硬,放不开,每跳一段就被领舞训斥。
她们在傍晚时分走了出来。柳安躲进拐角,看见柳清跟在队伍末尾。她们没有散伙,而是往北街的方向前进。服装批发市场对面的广场上临时搭建了一座舞台,前面挤满人群。柳清她们走进一个红色棚屋,在里面待了很久,出来时变成了相貌相仿的金发女郎,柳安只能依靠个头辨认柳清。她妆容惨白,表情狰狞,似乎在抵抗着身体的不适。
天色完全暗下来后,舞台上的音响装置震动了整座广场。柳安挤进嘈杂的人堆里,踮起脚凝视舞台。当柳清跟着节奏舞动裙摆,柳安立即低下了头,感觉脸在发烫。他不敢想象父亲看见这一幕会有何感受。
柳安被拍了拍肩膀,回过头发现是同班的陈斌和阿飞。陈斌嘲弄道:“没想到你爱看这个。”柳安说:“只是碰巧路过。”阿飞说:“得了吧,别不承认。”柳安岔开话头:“我听说你俩进轴承厂了,干得咋样?还要人不?”陈斌说:“有书不念,来干苦活,疯啦?你不是说将来想考什么文学系吗?”柳安说:“屁个文学,再这样下去我真得疯。”陈斌和阿飞不解其意地打量他。“我是认真的,”柳安对陈斌说,“叫你爸也带我进厂子吧。”
这时柳清她们跳完了开场舞,换了一身更惹眼的装扮重新登台,主持人不停地活跃气氛,观众拍手叫好。柳安感到一阵眩晕,找借口说自己得回家吃饭,赶忙告辞了。他今天的确没吃一口饭。跑回家的路上,柳安拼了命地想忘掉柳清在台上的样子,却怎么也挥之不去。
柳清回家已是晚上九点。柳安听见她推开卧室门的声音,立马走出去,扶着柳清的门框。“不许进来,”柳清大声道。
“我就站在这,”柳安说:“我和陈斌商量了,叫他爸带我进厂。”柳清说:“没必要,上你的学去吧。”
“不要,”柳安说,“咱爸以前总说你跳芭蕾的时候笑得最好看,我也这么觉得。”柳清吃惊地看着柳安,说:“刚刚你都看见了?”柳安说:“我不会和咱妈讲的。”柳清抬起手,铆足力气打了他一耳光。柳安摸着脸,委屈地说:“咱爸显灵那天,咱们都理解错他的意思了。”柳清说:“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,我不信这些。就这么着吧。”
“不行,我不想看你那样。”柳安说,“老规矩,每人二十颗珠子,明天一局定胜负。”
“幼稚。”柳清推开柳安,把门锁上。消气之后,她觉得刚刚出手有些重,想和柳安赔个不是。她走到柳安的门前站了一会儿,没有敲。海报左下角的便签不见了,换成了一张稿纸,写着一首短诗——
秋日的寂静中,枫树轻轻摇曳/红色的舞裙,一片片坠落/泥土深处,藏着来年的梦。
六
小卖部的六爷被一阵哄闹声打断午睡。透过一排八角糖果罐,看见十几个崽子在树荫下围成圈。六爷扯起嗓门说:“别老鹰捉小鸡了,等下你们都要被烤成烧鸡。”
“捉什么小鸡啊,”一个孩子喊道,“这是生死局。”六爷急忙跨出店门,发现人群的焦点是柳家两位小状元。他们面对面站立,怒目而视,各自手持一袋弹珠。一只装满空气的塑料袋在人群外面随风打转。
“赌什么?”六爷走到母亲身旁问。母亲含糊地解释了一番,六爷还是摸不着头脑,说:“不应该是谁赢了就去念书吗?怎么是输了去念书?”母亲说:“一言难尽呐。”六爷思索一阵,似乎明白了。他挤到人圈里,看着柳清,急忙用草扇给她扇风。“柳清,你糊涂呀,为什么和他比这个?我那枚‘神枪手’在他手里呢。”柳清瞥一眼六爷,继续死盯着柳安,说:“我不怕,开战吧。”
大家检查两人布袋里的弹珠,都是二十枚,随后宣布比赛开始。他们按照以往的规矩在地上摆放各自的弹珠,用石头剪刀布决定先手。柳清赢了。她单膝跪地,用拇指对准弹珠蓄力,“啪”一声,正中柳安的弹珠。柳清拾起战利品,开始下一轮射击。她接连命中目标,觉得索然无味,突然后悔答应与柳安对局。即便分出胜负也毫无意义,无非是闹了一出笑话。她站起身说:“算了吧,我想回去。”柳安说:“不行,要是不决出胜负来,咱妈又要为难了。”柳清说:“可我早就决定好了。”柳安说:“我也决定好了。大不了谁也别去念书。”母亲紧张起来,那种置身事外的轻松表情消失了。柳安说:“你要是看得起我,那就堂堂正正地赢我。”
柳清“切”一声,继续展开攻势。在打出第十枚的时候,弹珠被地面的碎石干扰了路线,跑歪了。柳安迫不及待地反攻,也在打出第十枚的时候失手。两人就这样展开了焦灼的拉锯战。柳安不断地挑选凹凸不平的路面放置弹珠,没想到柳清照中无误。战场的范围不断扩大,他们从小卖部打到了公路旁。“急死我了,”六爷走回小卖部,从糖罐里掏来一把水果糖,举在半空,“我今天阔一回,看谁能赢到这糖。”大伙儿兴奋起来,将地面拍打出节奏。
“我不稀罕,”柳安取出鲜红色的“神枪手”,像只猫科动物似的趴在地上,使劲瞄着三米远的淡绿色猎物。“神枪手”的准头从未让柳安失望,他习惯用它打出决定胜负的一击。可今天柳安求胜心切,试图用“神枪手”吃下柳清的最后三枚弹珠。
柳清又连输两枚,把布袋里最后一枚弹珠放在地上。她站起后觉得身体失去了重量,地面的热浪似乎能把她抬上天去。六爷说:“你输了也好。等你将来成了舞蹈家,可别忘了咱们。”
柳安的脑袋被晒得发晕。当他瞄准最后一枚弹珠时,一种奇妙的感觉冒了出来,自己仿佛在拙劣地模仿着父亲某年某天的击球动作。地面上暖乎乎的热气似乎是父亲的气息,这种感觉让柳安痴迷。他保持着姿势,细细地体会与父亲融为一体的感觉。
众人屏气凝神,看着“神枪手”以缓慢的速度前进,停在了目标前面一寸远的地方。这个结果让所有人始料未及。
“柳安你搞什么?”六爷说,“这次不算,再打一次。”柳清拍了拍裤子上的灰,说:“算了,我认输。”扭头推开人堆往回走。柳安拳头捶地,吼道:“你回来。”柳清继续走着,后脑勺突然一阵刺痛。“神枪手”落在地上弹跳了几下。是柳安扔来的。柳安说:“给你留点翻盘的希望不好吗?”柳清拾起弹珠,瞄准柳安脑门,却犹豫了,将手放下。“你们闪开。”她蹲下身子,愤怒地打出弹珠,拉开了新一轮的角逐。
比赛结束时太阳已经西斜,巷子里家家户户都起了炉灶。柳清、柳安和母亲一起往回走着。十三粒水果糖被他们分成了三份,母亲一粒,柳清和柳安各六粒。“就知道逞英雄,”柳清嚼着糖说,“你的技术比咱爸差远了。这样让来让去的,哪能有结果?”柳安说:“你还不是一样?”柳清“切”了一声,拍了下柳安的脑袋。
“我有办法,”柳安说,“你去学校上一周课,我再替你上一周,回来交换学到的东西。”柳清翻了个白眼,说:“幼稚。”柳安说:“那就再比一场”柳清说:“随你。”
“比谁先回到家,谁输了就去念书。”柳安说罢撒腿往巷子深处跑去。“耍赖皮!”柳清追着喊道,“再不停下,我就把你的烂诗念给整条街的人听!”柳安说:“当心我把你的事情告诉咱妈。”两人追跑打闹起来,柳清用灵活的舞步躲闪柳安,在巷子里画出了优美的蛇形曲线。
望着跑远的姐弟二人,母亲十指相扣,小声道:“老柳啊,他们都长大了,你在那头就放心吧。”
责任编辑:梅不谈
